从省锡中分部的南校门踱步而出,朝东,经过两个店面,就是阿姨馄饨店。阿姨馄饨店,从店名来看,一定是中年阿姨经营的,主打的应该是家常馄饨。但只要到店消费过,就发现其实不然。打理馄
从省锡中分部的南校门踱步而出,朝东,经过两个店面,就是阿姨馄饨店。
阿姨馄饨店,从店名来看,一定是中年阿姨经营的,主打的应该是家常馄饨。但只要到店消费过,就发现其实不然。

打理馄饨店的是一对中年夫妻。老板约摸四十来岁,已经有些谢顶,说话柔柔的;老板娘齐耳短发,说话简洁,动作麻利,一看就知道精明能干。夫妻之间的对话我是一句也听不懂。后来聊天才得知,他们是泰州那边人,因为儿子在无锡工作,夫妻俩才决定背井离乡,举家搬来无锡。他儿子我是见过的, 一个英气勃勃的小伙子,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公司就职。因为在无锡买了商品房,夫妻俩就开了这爿点心店谋生。
除了早晨和中午提供馄饨外,他们赚钱主要靠的是中餐和晚餐。除了冬天之外,他们还做夜宵。
刚开张时,阿姨馄饨店顾客盈门,生意兴隆。说实话,顾客中绝大部分都是分部的教工。吃腻了学校食堂的包子和稀饭,厌烦了食堂中午的那几个很少更换的家常菜,阿姨馄饨店提供了另一种选择。

小店的馄饨确实不错,尤其是馅儿,青菜肉馅,新鲜,味道鲜美,而且皮薄馅多。清汤馄饨配的是肉汤,加上小葱;拌馄饨,浓油赤酱,很合无锡本地人的口味。这样一传十,十传百,分部食堂里顿时少了很多就餐的老师。
记得当时我正好在初二备课组,搭档的是包敏韵老师和丁军老师。于是,我们就把备课组活动的场所搬到了馄饨店里,中午相约在那儿小聚餐。
不过夫妻俩烹饪的技艺不行,除了一个红烧鱼头还可口之外,其他的就太咸了,也许是他们家乡的重口味吧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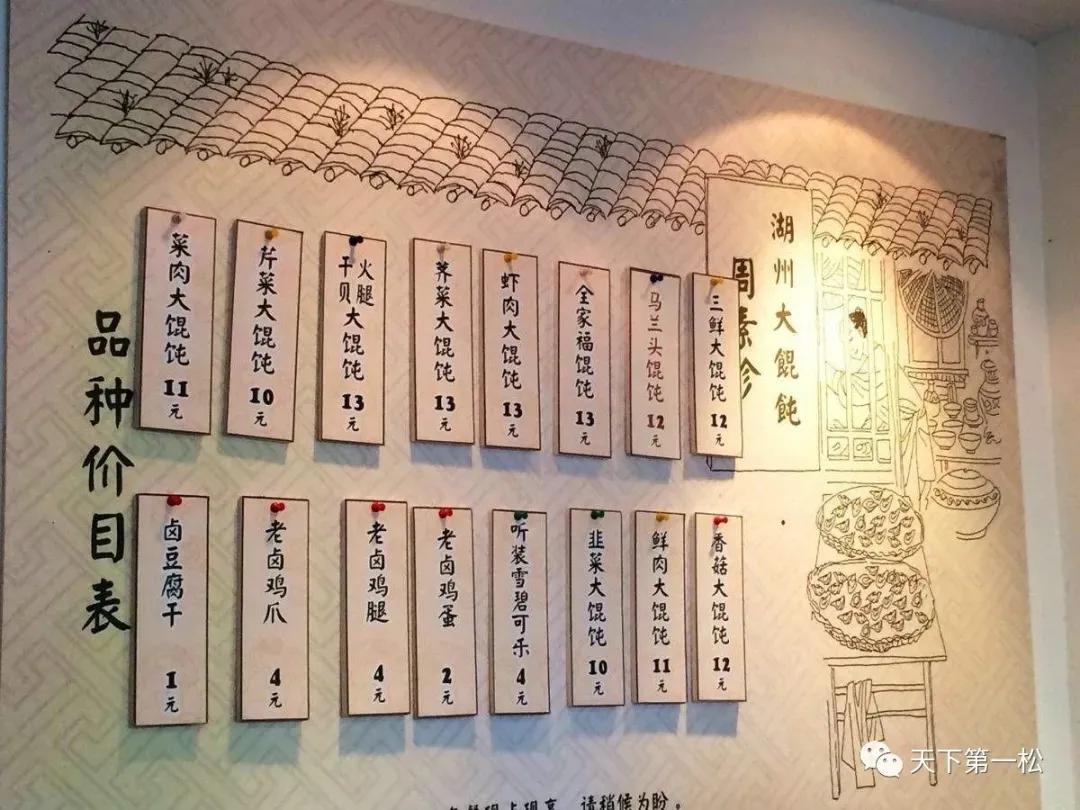
有一次,因为处理学生违纪,到食堂用餐太晚了,于是我就独自一人跑到店里随便填饱肚子。我记得我点了最喜欢的青椒炒肉丝和红烧粉皮。因为中午还要巡视学生的自修,我匆匆扒了几口饭,连菜也没吃完就付钱回校了。
傍晚时,我和几个好友相约到店里喝点小酒。一进门,老板就笑眯眯地对我说:“范老师,你中午吃饭太匆忙了,连你最喜欢的粉皮都没吃完,我给你放在冰箱里了,待会热了帮你端上来。”我大为惊讶,老板怎么知道我最钟情粉皮的。“我看你每次来吃饭都必点粉皮,就知道你最喜欢了。所以就帮你留着了。”老板看出了我的疑惑,连忙解释道。我心里一热,这个老板还挺关心我的。

还有一次,周末到校上班时,我从家里带了两瓶好酒,准备有空时邀上几个好友到馄饨店里小酌。但那一周很忙,就这样拖下来了。一直到周四傍晚才得空,于是,我就约上王峰、韩国庆和张静建到店里喝酒。
我们四个每人半斤,边喝边聊。这边我和静建互敬,那边峰弟和国庆对酌。但那天,好像峰弟和国庆热情不高,跟往日大不相同。要知道,国庆兄弟喝酒一向特别爽快,他是喜欢把自己先搞趴下的主。峰弟虽然酒量差一点,但最擅长把半斤喝成一斤,咋咋呼呼劝酒是他的拿手好戏。不过,我也没多想。很快,半斤老酒就下肚了。酒酣耳热之际,我和静建商量着再来一瓶, 四人平分,静建赞同,正准备拿酒,那两个家伙连连摇手,坚决不肯再开一瓶了。奇怪,这两个怎么就转性了呢?
事后我才知道,原来那一顿老酒,峰弟和国庆喝的一直是自来水。虽然是从酒瓶里倒出来的,但里面装的确实是自来水。此前那一瓶酒,他俩早就趁我不备之际,开了偷偷喝掉了。试想,我和静建喝得热乎乎,晕乎乎,他俩喝自来水,而且正值冬季,这一瓶自来水把他俩喝得透心凉,哪还有心思再来一瓶呢?
后来,阿姨馄饨店的主打馄饨质量渐渐下滑了,兴许是生意好了,老板夫妇懈怠了。再后来,学校搬迁到堰桥,我们再没机会去那儿了。
一日,在学校食堂竟然偶遇馄饨店老板,他来学校食堂打工了。一问之下,原来天一实验搬到那儿之后,生意一天不如一天,小店撑不下去了,他只能来实验学校食堂谋一份差使了。
不过,老板对我们这些分部的老人还是一如既往地热情,每次打饭,都和我们打招呼。他毕竟是个有情义之人。

若干年之前,一次和妻子路过分部旧址,我特意下车,想看看分部,看看那个馄饨店,但所有的记忆都不复存在了。崭新的商品房建起来了,高大,富丽,估计价格不菲。两边原来的店铺全部拆光了,新店铺装修一新,这块土地上没留下省锡中分部的一点痕迹。
那天,我和妻子在分部周围徘徊良久,最终只在柏庄街上找到了以前的一点影子,心里感慨而伤感。时间真是一个残忍的记忆杀手!但不管他如何锋利,我们对分部的爱和怀念却是它无论如何也削凿不了的。
谨以此文,怀念我们在分部时的那些美好时光。